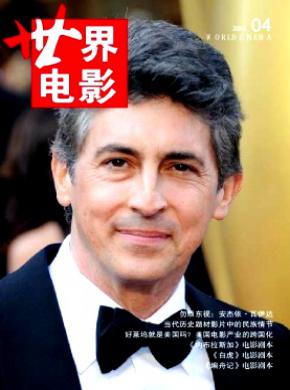世界電影投稿論文格式參考:真理、想象和歷史記憶的政治:戈達 爾、本雅明和瓦爾堡*
關鍵詞:
作者:文/[葡萄牙] 米格爾·梅斯基塔·杜阿爾特;譯/祁 勇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隱喻書寫:形象與思想
在戈達爾(Godard)的影片《小兵》(Le Petit Soldat,1963)的一個場景中,一 個搖攝鏡頭展示了一組散布張貼在墻上的有關戰爭的圖片、廣告和軟色情圖片。與此 同時,主角布魯諾·福雷斯特頓(Bruno Forrestier)說道:“早上7點。一組從世界各 地拍攝的快照像噩夢一樣從我身邊掠過。巴拿馬……羅馬……亞歷山大港……布達 佩斯……巴黎……”這些快照對于福雷斯特頓來說似乎是一個夢境,因為它們涉及 一種夢境的意識模式,其中現象的多樣性是以一種碎片化的狀態呈現的。
延續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和其他魏瑪知識分子 的思路,戈達爾和本雅明(Benjamin)兩者的大眾文化觀都被視為一種歷史批判 模式而得以接受。正如克拉考爾所指出的那樣,本雅明認為“知識來源于廢墟” (Kracauer 1995,264),戈達爾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其中歷史事件和文化碎片 被視為廢墟,從等級制度以及工具理性和時間連續性的同質化原則中被解放出 來,從而催生出新的文本并呈現出易讀性。此外,在戈達爾和本雅明兩者的認識 中,影像獲得了克拉考爾所稱的“小物質粒子”的地位,這些粒子指向本質或思想 (Kracauer 1995,263),而不僅僅是為各種現象提供一種懷舊的和傷感的呈現。
本雅明在他的《認識論-批判序言》(Epistemo-Critical Prologue)中斷言 “理念不以其自身為表征,而是在具體元素的排列中唯一的表征……”;他接著說 道,理念相當于對現象的“虛擬排列”以及對現象的“客觀闡釋”,或者以星座作 為類比,“理念之于客體正如星座之于群星”(Benjamin 1998,34)。
同樣,對于戈達爾來說,星座的概念與和解(rapprochement)的概念構成了 他的電影意象譜系的基石。在影片《老地方》(The Old Place,1998)中,戈達爾 直接論述了本雅明的歷史哲學——作為他的鴻篇巨制《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1988—1998]的一個額外段落——他說道:“此概念就是那個和解的概念。 這就像星星在彼此遠離的時候也會和另一些星星彼此靠近從而形成一個星座,某 些事物和思想也會以這種方式彼此靠近,進而形成一個或多個意象。”(Godard cited by Witt 2013,183)
因此,戈達爾和本雅明都認為意象的概念不可以僅僅簡化為經驗的視覺表征。 它本質上是一種思想的意象,一種辯證思維的意象,這分別證明了蒙太奇在他們的 電影理論和文學理論中的重要性。但人們也必須意識到,在兩位作者的認識中,辯 證意象的潛在關聯也是一種中斷的、有阻力的和不連續的潛在關聯。這就是為什 么戈達爾在電影中通過蒙太奇段落所建立的兩個或多個意象之間的間隔,本質上 被理解為一種思想的拓撲表現方式。這有力地呼應了本雅明的論斷,即“思維不僅 包括思想的流動,也包括思想的停駐”,“在一個充滿張力的星座構型中”突然停駐 (Benjamin 1969a,262-263)。
在瓦爾堡(Warburg)的《記憶女神圖集》(Mnemosyne Atlas,1924—1929) 中,嵌版的黑色空間同時分隔和匯集了各種藝術作品的復制品,在這里黑色空間可 以理解為典型的象征。正是這種間隔使得瓦爾堡能夠將有關藝術史和西方文化的 多個形象聯系起來,使他能夠繪制出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具有強烈感染力的形象的 遷移、變化和遺存的過程(Didi-Huberman 2002,496)。因此,同樣在瓦爾堡的認 識中,形象成為了一種可以移動的粒子,不斷進入由其他形象和理念構成的可變的 和辯證的星座。在各個地方,形象本質上都是可變化的和可移動的思想單元。這就 是瓦爾堡使用圖釘在圖集的嵌板上散布照片復制品的原因。這些圖釘的功能是作 為一種基礎的但十分高效的技術物料,服務于辯證蒙太奇的創作,創作出潛在的 具有無限可能的閱讀物,正如同戈達爾和本雅明的觀點,蒙太奇是一種將各種各樣 明顯不相關的內容對列并創造類比的方法。
當考慮到這些作者的作品時,影像和文字之間的關系是對等相關的。在所有 這些作品中,都有可能確認影像和文字之間、形象和文學之間的這種相互關系,這 種關系削弱了一個元素相對于另一個元素二元的和等級上的特權。
的確,如果在戈達爾的例子中,將電影屏幕視為一張空白頁(Bellour 1999, 126),那其中視聽影像和插卡字幕則以一種“短語結構”或“并聯句式”的形式結合 在一起,正如朗西埃所說(Rancière 2003,72),本雅明的手寫草稿表現出了對頁面 結構和圖形形象的獨特興趣,這一方式具有典型性。通過將數組單詞組合成簡略圖 示和短語構型來保持某種圖形關系,其中一些手稿將本雅明的成就轉化生發為重 新定位思想的意象辯證關系,從而超越了書寫頁面預先確定的幾何形狀和傳統語法(Schwarz et al.2015)。喬治·迪迪-于貝爾曼(Georges Didi-Huberman)在瓦爾 堡的《記憶女神圖集》和同時期用于詳盡闡述該作品的手稿之間建立了類似的對應 關系。根據對一系列手稿的分析,迪迪-于貝爾曼指出,瓦爾堡認為理念被置于白頁 之上,就像圖像被分布在圖集的黑色嵌板上一樣,包括對短語和一系列單詞和圖像 的概括的和簡略的呈現。這與戈達爾的電影蒙太奇相似,它是在各種不同的影像和 文學節選的概括與啟發的交匯中得以持續的。因此,戈達爾的表述是,在討論“走向 言語的方式”時,電影成為了“一種思維方式”,它是為思考而生的(3A)。
總之,對于戈達爾、本雅明和瓦爾堡來說,書寫大體上被理解為一種將可見實 體與理念聯系起來的思維的和感知的方法。對于他們所有人來說,書寫剔除了慣常 的易讀性,成為貝魯爾(Bellour)從戈達爾電影中提煉出的特征那樣,本質上是可 見-易讀結構的對象(Bellour 1999,126)。
想象、記憶和真理
馬修·蘭普利(Mathew Rampley)準確地指出,本雅明和瓦爾堡都認為現代性 是當代文化在物質和理念層面發生轉變的時刻。與歷史發展的慣常敘述相反,他們 接受了“文化空間的理念”,這一理念維系在視覺和文本的共時關系中,重新調整 了歷史空間和時間的表征方式(Rampley 1999,96-97,113)。
因此,對于這些藝術家-歷史學家來說,就像戈達爾一樣,文化空間與作為歷史 時間的另一種替代模式的記憶概念密切相關。我們已經看到,在本雅明和戈達爾 那里,辯證思維把事件從同質的歷史進程中爆炸開來:碎片從其原有語境中剝離出 來,重新組合成一個新的由意義和時間構成的 星座,提供了歷史解釋和文化體驗的新模式。 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本雅明認為星座 是發生在睡眠和覺醒之間的理念的一元性結 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雅明的《拱廊街計 劃》(Passagen-Werk,1927—1940)的法語版 本中使用的“réveil”一詞,在一定程度上將 合理性賦予了一個短暫的、具有閾限的意識空 間,它直接將歷史學家與記憶的建構性失敗、 非連續性和缺失聯系起來。
但是,如果本雅明的辯證方法的確證實了 過去的對象所處的歷史情境,那么實際上它主 要關注的是對它們進行具體分析和現狀分析 的時刻。因此,他認為記憶是一種同時具有思 維和情感因素的積極和持續的過程。對于本雅明來說,歷史認知的特定時刻涉及已經發生的轉瞬即逝的存在和“正在體驗這一 覺醒世界的現在”之間的辯證法(Benjamin 1999a,398)。事物從其過去中被抽離 出來,在當下,在已經覺醒的此時此刻完全變成現實。在集體經驗和文化記憶中, 覺醒的時刻是一個顛覆性的時刻。在這一時刻人類擦亮眼睛并認識到現在和過去 星座的重要性。“就在這個時刻,”本雅明寫道,“關于這種意象,歷史學家承擔起 了釋夢的任務”(AP,464;N4,1)。
在這里本雅明顯然指的是弗洛伊德(Freud)的《夢的解析》(Traumdeutung)。 根據本雅明的觀點,唯物主義歷史學家應該通過批判性分析來解釋大眾文化中的象 形符號,就像分析師解釋記憶的痕跡一樣,即夢境和失敗行為中被壓抑和隱匿的內 容,這些內容通過一系列錯位、間隔和符號重構浮現在意識中。在《拱廊街計劃》的 K卷(Convolute K)中,本雅明借鑒了皮埃爾-馬畢(Pierre Mabille)的觀點,認為歷 史的過往是一個無意識的隱匿空間,由大量的事物構成,這些事物在不同的時代進 程中被散布和遺忘,因此必須通過富有想象力和批判性的思維來對其進行解讀和重 新詮釋。
例如,在《電影社會主義》(Film Socialisme,2010)的第三部分,戈達爾匯 集了大量的檔案影像和電影片段,成為歷史認知的考古元素。這方面的一組例子 是:將愛森斯坦(Eisentein)的影片《戰艦波將金號》(Battleship Potemkin, 1905)中著名的敖德薩階梯的段落與一群兒童現場實地游學的當代影像并置;將 1937年馬爾羅(Malraux)關于巴塞羅那共和軍抵抗運動的影片《愛》(L’Espoir) 的片段、一場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比賽的電視鏡頭(電視轉播的壯觀場面導致的集 體異化)與街頭政治示威的場景通過一段蒙太奇混剪在一起;將讓·吉內特(Jean Genet)講述他與巴勒斯坦戰士遭遇的回憶錄,以及巴以沖突的新聞照片和希特勒 的圖像剪輯在一起;最后,將1943年在那不勒斯拍攝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鏡頭與關 于公元前5世紀古典希臘史詩般戰爭的故事片片段混剪起來。
通過混合、并置和轉化相結合,這些影像如同在歷史層面產生猛烈爆發,在當 下的影像中熊熊燃燒。事實上對于戈達爾和本雅明來說,歷史的過往構成了一個 潛在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所有的變革、文化和事件都匯集在一種無形的、異質 的記憶空間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于兩者而言,記憶發揮了一種解體機制的功 能,因為它處理的是歷史學家夢寐以求的并且相對傳統務必重構的過往的碎片。因 此,在本雅明那里,就像在戈達爾和瓦爾堡那里一樣,認為時間和記憶的元心理學 (metapsychology)能夠聯系和揭示歷史的多個層面,如果沒有這種元心理學,就 不可能有歷史的存在。
在這方面,普魯斯特(Proust)的非意愿記憶對本雅明和戈達爾有根本性影 響。對兩者來說,時間都與一種普魯斯特式的維度有關,其中事物在時間層面占據 的位置與其在空間層面的位置是不可比較的。正如本雅明所提到的,普魯斯特所有試圖通過純粹的推理來喚起過往的嘗試都是無效的。即便是游走于回憶中的地 方和真實的地方也不會有助于這種恢復。挖掘和穿透被土地覆蓋的事物是相當必 要的。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回憶是“經驗之物的媒介,正如同土地是埋于地下古 城的媒介一樣”(Benjamin 1999b,576)。
在《電影史》2B中,戈達爾明確地提到了時間和歷史的這種考古和記憶的特 征。戈達爾挑釁性地將“trou”一詞分離出來,這個詞匯截取于普魯斯特的巨著 《追憶似水年華》(In Search of Lost Time,1913—1927)最后一卷的標題“Retrou-vé”。正如在他的達達主義劇本的語言中習以為常的那樣,戈達爾賦予這個 詞匯一種多義性和超越常規的意義。其語義價的展開,既表示具有象征意義的考古 刺探工作所產生的穿孔,同時也表示攝影機鏡頭的打開,使人們能夠通過事物和時 間的斷裂來理解現實和歷史。戈達爾在《電影史》的同一段落中提到:“電影必須 為哽在喉嚨里的文字而存在,為挖掘真相而存在。”這并非偶然。
我們必須密切關注戈達爾將現實與歷史記憶聯系起來的手法。接下來在同一 序列中,戈達爾面對觀眾使用了一個高深莫測的表述:“電影是商品,電影必須被 燒掉……但要小心內心的火焰。物質與記憶。藝術如同火焰。它源于所燃燒之物。” 與此同時,畫面中戈達爾從他的圖書館里拿起一些書,他一個接一個地引用了這些 書的名字,還有戈達爾1967年的影片《周末》(Week-end)的片段,在這個片段中, 我們看到一對夫婦從爆炸引起的火焰中走出來,這些畫面與屏幕上的文字結合在 一起,我們從中讀到:“我們在夢想上欺騙自己,是為什么而作序?”這句話出自本 雅明的《青年的形而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Youth,1913—1914),這是一篇 關于夢想、愛情、語言和時間的公開的哲學詩歌文本。
戈達爾對本雅明的引用大體上可以從他對歷史認知的理解的角度來解釋,這 是一種令人驚奇和驚訝的體驗,揭示了集體的和個人的主體最秘密和最密切的東 西。但如果我們關注戈達爾之前的表述,那么似乎他本質上指的是藝術的破壞性特 征,以及恢復真理的可能性,因為真理可以在解釋和接受占主導地位的傳統的廢墟 中重新出現。
有一種觀點認為藝術應被理解為一種表現歷史苦難的恐怖的活動,在戈達爾 看來,應該對這種觀點予以駁斥,這一點很重要。這是他明確拒絕的東西,例如,在 1998年的影片《老地方》中,他批評了一場描繪戰爭和種族滅絕悲慘后果的紀錄照 片的藝術展示。
在《電影史》1A中,戈達爾將“藝術在浴火中重生”的評論與安杰伊·蒙克 (Andrzej Munk)1963年的影片《乘客》(the Passenger)中由猶太囚犯臨時組 成的管弦樂隊的影像(這一場景又與倫勃朗[Rembrandt]1630年的自畫像疊化在一 起,此畫以其驚奇和著迷的表情而著稱),以及馬蒂亞斯·格呂內瓦爾德(Matthias Grunewald)約1510年的宗教繪畫《耶穌誕生》(Nativity)的細節并置起來。有時會有觀點認為,藝術是大屠殺災難的頂點,對戈達爾來說,得出這樣的結論是荒謬 的。蒙太奇表明,正如藝術之美所包含的真理是通過充分展現其秘密的且不可言 說的維度來揭示的一樣,歷史認知也蘊含著一個不可侵犯的維度:通過這一維度, 歷史真理在緊密的探索和令人驚奇中被揭示出來,將主體與秘密且不可侵犯的領 域聯系起來,并肯定藝術和詩歌是抵抗壓迫性權力和集體異化形式的典范。
在戈達爾的作品中,蒙太奇是一種對真理的演練,這種真理是在一系列相互 聯系與轉化的影像之中遇到的。其中蒙太奇通過碎片化的方式導致敘事和主體性 的去中心化,橋接了歷史敘事與物質現實呈現之間的鴻溝。因此,其政治的和倫理 的緊迫性與賦予觀眾在意義建構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能力有關,這種意義與世界的 現實密不可分。因此,戈達爾在影片一開始就將“Histoire”(歷史)一詞進行了拆 分,創造了“toi”(你),并在不同的章節中重復使用。觀眾不是被動接受標準化和 官方版本的歷史敘事的一群人,而是被賦予了“不可估量的自由”的“具有創造力 的一群人”。正如我們在《電影史》4A中聽到的那樣,世界的焦慮不安只有在向我們 提出問題并迫使我們每個人采取行動和選取立場的過程中實現具體化的那一刻, 才能獲得它們可感知的密度。
因此對于戈達爾來說,關鍵之處當然不是整合與約束形而上學的真實,而 是一種關于發現和倫理選擇的行為,這種行為是在歷史對象的時間的延誤、 間隔和自相矛盾的殘存中得以尋求的。這與瓦爾堡所說的藝術史形象的遺存 (Nachleben)相似。通過姿態和表情的強度來表現人類的悲情,瓦爾堡通過對 共有的和沖突的情緒反應的表現來揭示藝術史的形象連接多個時間和地點的能 力,形成了瓦爾堡的“情念程式”(Pathosformmel)概念的終極含義。
至于戈達爾,通過將電影的影像與繪畫的圖像混剪在一起,并通過激發它們 的情感與理智的回響,作為恢復歷史事件真理的最終可能性,他實現了對瓦爾堡的 情念程式的重新激活,同時,他將他的影片置于電影、藝術和哲學的交叉點。而且 通過這種方式,他也回應了本雅明理論的另一個基本前提:哲學是“真理的表征”, 而不僅僅是獲得連貫和穩定知識的指南(idem,28)。
虛擬、遺忘和真理的必要條件
根據恩斯特·西格(Ernst Seger)的《伊西斯女神的面紗》(The Veiled Image of Sais,1897),本雅明認為,真理并不是“通過被暴露”而揭示出來的。 真理構成美的內容并且是在一個過程中顯露出來的。本雅明將其比喻為“當它進 入思想領域時外殼的燃燒殆盡”,他繼續說道,“也就是說,這是對作品的一種破 壞,其中作品的外部形式達到了最輝煌的照明程度。”(本雅明1998,31)
本雅明的論斷將我們與上文提到的《電影史》2B中的評論聯系起來,在其 中我們聽到:“物質與記憶。藝術如同火焰。它源于所燃燒之物。”人們不能忽視的事實是,戈達爾直接暗指了柏格森(Bergson)的《物質與記憶》(Matière et mémoire,1896)。在他的書中,柏格森區分了簡單或行為記憶和純粹記憶。前者與 分為先后的動作和反應之間的感知運動系統有關,后者涉及純粹的知覺和嘗試作 為綿延(durée)的記憶之間的瞬間巧合(Bergson,1919,79-89)。盡管如此,在柏 格森看來,作為綿延的記憶并不是在公園里散步。他認為其中包含了一種嘗試,一 種由于線性時間的習慣性機制的中斷而產生的猶豫,這表明了記憶過程的無效。 然而,這種猶豫體現在情感的印記之下,與一種思維活動的形式聯系在一起,柏格 森和普魯斯特都將這種活動與創造和發明思維的潛力聯系在一起。在這兩種情況 下,綿延都涉及記憶形象的物質性以及聯想和創造類比的精神活動。
正如利科(Ricoeur)所指出的,柏格森認為被記憶的過往的留存與潛意識的無 效或遺忘的狀況有關(Ricoeur 1997,570)。遺忘不是被理解為記憶痕跡的簡單抹去 或衰減,而是被認為是一種未被察覺的虛擬的能量。因此,關鍵是對柏格森純粹虛擬 性的考慮,這種純粹虛擬性關注的是在變化過程中所實現的東西。總之,它是一種實 虛回路的雙向流動,能夠使流動中的多種類構成的影像與其暫存狀態在時間的持續 中共存。這就是為什么戈達爾會在《電影史》4A中說道:“任何人想要保留記憶都必須 寄托于遺忘,冒著風險寄托于這種絕對遺忘,并且寄托于這種轉變為記憶的良機。”
這不也是瓦爾堡作品的核心嗎?通過向希臘記憶女神(Mnemosyne)致敬,讓她 出現在《記憶女神圖集》的書名中和他的圖書館入口處,瓦爾堡將記憶的藝術與想 象力和創造性思維的過程聯系在一起。根據喬爾丹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 瓦爾堡是他的忠實讀者)的說法,作為九位繆斯女神的母親,記憶女神只承認自己想 到了之前依靠想象創造出來的形象。因為只有通過喚起足夠強大和具有創造性的形 象,思想才有可能從遺忘中恢復過往的真實內容。這就是為什么希臘單詞“lethes (λiθη)”的詞源,其含義為遺忘或隱藏,與真相或真理(αλθεια)密切相關:前 綴“an-”是單詞“un-forgetfulness”和“un-concealment”合成的基礎,表示揭 示真相的過程,正如“anamnesis”指的是喚起(ana)曾經被遺忘記憶(mnesis) 的行為。換一種說法,過往的遺存與鐫刻在情感印記下的記憶的持久性和持續 時間有關,也就是瓦爾堡依據理查德·西蒙(Richard Semon)的心理生物學理論 (psychobiological theory)所定義的“情感體驗的印記”(engram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Warburg 2009,278)。根據利科的觀點,我們可以說,如果一段記憶得 以遺存,那是因為它在某一時刻丟失了,被遺忘了;但即便如此,記憶也能被恢復并被 認為是個人或集體的某些真相和基本情況,這是因為它的形象得以遺存。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利科將記憶的現象學和歷史的認識論與真理的一個必要 條件聯系起來,這個必要條件通過柏格森的記憶研究的成果而得以揭示(Ricoeur 1997,66)。記憶區別于純粹的幻想和所有其他思維過程的是它與真理的必要條件 之間的特殊關系。這一點是在蒙太奇所造成的困難中呈現出來的,并且引起了一些作者的評論。它既可以揭示分散的碎片的幸福相遇,也可以揭示不明智選擇的致命 接合(“蒙太奇,我美麗的憂愁”,戈達爾在《電影史》中如是說)。
的確,戈達爾和本雅明兩者的歷史學說,還有下文將要談到的瓦爾堡的歷史 學說,都是以真理的必要條件為支撐的,在他們的證據的紀錄價值和大量的虛擬 聯系中,其中的事件被同時呈現出來。對他們來說,形象是描繪有意識的和無意識 的文化過程的物質和精神的記錄(Woodfield 2001,4)。他們的作品通過隱喻、象 征、詩意典故和寓言與歷史真理建立了間接的關系,使我們更加接近真理:也就是 說,更加接近當下那些影響到我們,與我們有關的事物的意義。正如本雅明所說, 侵入我們的夢境,并要求我們把覺醒解釋為一種發現的行為:批判性和想象力思維 的“當下性(Now)”(Benjamin 1999b,831)。借用本雅明的話來說,這不是按照事 情發生的真實情況來描述的問題;它與意識到和察覺到某事偶發和必發有關,暗示 我們成為歷史進程的代理人和見證人(Ricoeur 1997,66)。
自反性和意圖的死亡
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可能識別出一種自傳式的情感,這種情感在本雅明、 瓦爾堡和戈達爾的歷史學說中是共通的,并通過一種勇敢的脆弱表現在他們身上。正 如塞西莉亞·賽亞德(Cecilia Sayad)所指出的,戈達爾通過電影進行自我驗證并構建 自己的身份。戈達爾經常在他個人圖書館的書架前坐在一張用于打字的書桌旁陷入沉 思,他把電影定位為一種元自反性(meta-reflexive)的質疑,這種質疑涉及作品的構 建,與影像和蒙太奇交叉對作品的重要性,以及他作為作者的作用:因此,他為電影提 供了一種與意義和解釋路徑的構建并行的表演和懺悔成分(Sayad 2013,xxii)。
如果戈達爾曾經被比作歷史方面的本雅明之天使,無助地凝視著歷史的災難 (Dall’Asta 2007,352)(“這一面總是有罪的,或者被詛咒的,正如瑪格麗特·杜 拉斯[Marguerite Duras]所說,她說我被詛咒了”,我們在《電影史》2A中聽到這 些),那么在瓦爾堡的案例中,對西方文化的戲劇性沖突和矛盾的理解與他對自己 個人精神疾病和精神分裂癥史的自我意識密切相關。
但瓦爾堡無可否認的個人脆弱卻自相矛盾地包含著一種沖動的力量,這種力 量促使他對美學和藝術史的研究需要一種非正統和非形式主義的方法:一種包含了 “心理歷史學”(psychological history)的方法(Warburg 2009,277),這將使 他能夠認識到(通過將個人病理敏感性延伸到對集體和社會模式的識別)界定西 方文化核心動力和模糊性的相互對立的力量之間的沖突。用瓦爾堡的話來說,這是 一種精神分裂的文化,在費解和理性、犧牲和哀悼、侵略和防御、狂喜和抑郁之間 分裂(Warburg 2007,314)。
根據他的觀點,這種相反的文化力量被印刻在藝術史的形象之中,并被典型 地象征為“赫利俄斯向太陽上升,珀耳塞福涅向深處下降”(Warburg cited byIversen 1998,220)。瓦爾堡沉淪于情念運動和圖像的無序散布,并最終走向面臨 “完全喪失自我的風險”(Didi-Huberman 2007,13-14)。但這種個性化的散布和 個人崩塌的原則也引起了歷史認識論的靈活化、具體化和去中心化。一個能夠肯定 自我的心理和生理層面不確定性的人,其所想與歷史實證主義中成功的、權威的和 包羅一切的自我領域完全對立(Cf.Iversen 1998,223)。
在這方面,戈達爾引用了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一句話,其中 我們讀到:“上帝,我多么痛苦!擁有如此強烈地感受一切的天賦真是太可怕了!” (3B)表明對他來說,和對瓦爾堡一樣,在記憶和歷史研究的思維活動中含有一種 不可減少的悲情。(因此瓦爾堡把記憶女神[Mnemosyne]和阿特拉斯[Atlas]結合 在一起,阿特拉斯肩上扛著極為沉重的天球,是苦難的經典代表)。
沿著布克哈特(Burckhardt)和尼采(Nietzsche)的思路,瓦爾堡將自己定 義為“歷史地震學家”,能夠察覺和播報歷史的地下運動中最強烈的振動。在戈達 爾和瓦爾堡的作品中,歷史學家都作為一種“感光表面”來呈現,正如阿蘭·米肖 (Alain Michaud)所說的那樣,通過這一方式,“文本和形象從過去浮現出來,并 在當下自我展示出來”(Michaud 2007,260)。
這正是本雅明對“意圖的死亡”的定義,與個人意圖和在真實歷史敘述中作者 特權的消除有關。對本雅明來說,“真理是一種無意圖的存在狀態,由理念構成。 因此,真正的接近真理不是接近意圖和知識,而是完全沉浸和吸納于其中。真理即 意圖的死亡”(Benjamin 1998,36)。
在本雅明看來,過往的可引用性回應了這一要求,在這種意義上,文本碎片會 以一種“自由浮動狀態”相互反映,完全逃避作者的掌控(Arendt 1968,47)。極 為有趣的是,在《電影史》2B中,戈達爾引用了葡萄牙電影攝影師曼努埃爾·德奧里 維拉(Manoel de Oliveira)的話:“這就是我喜歡電影之所在。大量的華麗符號 沐浴在缺少解釋的光芒中。”
對本雅明來說,過往的可引用性是在對過往的傳播中取代傳統權威的構想方 法。正如戈達爾的引用方法顯然得益于本雅明的方法,過往通過引文的集合獲得了 客觀和真理的易讀性,通過圖解結構和互文結構相互關聯。這些圖解的關聯是由 作者繪制的,但它們的意義和動態最終將由讀者來推進。然而,本雅明卻將其視為 文本的一種客觀的易讀性,因為它指的是與形象相關的思想碎片完全的具體性和 實質性,這種思想碎片呈現出與傳統抽象推理慣常過程的對立。
不可避免地,這讓人想起了本雅明對他的《拱廊街計劃》方法論的著名總結:“這 個計劃的方法為:文學蒙太奇。我不需要說些什么,僅僅是展示。我不會偷竊任何貴重 物品,盜用任何精妙的配方。但我也不會盤點那些破布、垃圾,而是允許以唯一可能的 方式——通過使用它們——去充分展現其自身價值。”(Benjamin 1999a,460;N1a,8)
本雅明的碎片有力地證明了戈達爾的論斷:“歷史學家不是去調查,而是去發現”;“保護影像不受語言的影響”的唯一方法就是“真正去使用它們”,就像我們在 《電影社會主義》第三部分開頭聽到的那樣。保護影像不受語言的影響,就是取消 了實證主義解釋的語言模式,正如本雅明的引用原則和文學蒙太奇為現有的歷史著 述和歷史經驗的模式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如同在瓦爾堡那里,也在戈達爾和本雅明 那里,唯物主義歷史學家的任務由此與詩人的任務類似。因此,本雅明承認波德萊 爾(Baudelaire)的詩歌創作方法的重要性,波德萊爾的文學作品與馬奈(Manet) 的現代繪畫(3A)一起構成了戈達爾最重要的“原型電影人物”之一(Morgan 2013, 164)(2A)。通過從時間和現實的多個層面中選擇對象,詩人將其從各自功能中解放 出來,在與形象相關的聯想和類比,或《感應》(correspondances)的引導下,以一 種碎片化和具有高度暗示性的形式對其進行重新整合。因此,詩人是一個感光的表 面,一個專業的攝影師,正如本雅明所認定的那樣,能夠有預見性地揭示過去和未 來的形象,包括它們所有的細節和豐富多彩的變化。
外部的思想
正如菲利普-阿蘭·米肖所證明的那樣,瓦爾堡實際上借用了胡戈·馮·霍夫 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題為《詩人與我們的時代》(The Poet and the Present Time,1906)的演講中“歷史學家-地震儀”的概念,在演講中,他將詩 人比作記錄和傳送世界震動的地震儀。根據霍夫曼斯塔爾的說法,這并不是說詩人 思考所有的事物,而是事物決定他們并支配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勝過最直接的個人 意圖(Hofmannsthal in Michaud 2007,260)。
這些或多或少的隱喻性表述所反映的是柏格森在他關于時間和記憶的作品中 已經能夠察覺出來的東西。作者在這里指的是柏格森關于時間無意識的概念,它是 一種擴展的主觀軌跡,覆蓋了過往的全部,擺脫了人類心理學的限制。因此對柏格 森來說,不是時間屬于我們,而是我們屬于時間。我們身處在一種記憶世界中,它涉 及一個純粹的虛擬空間,也就是說,一個尚未建立和尚未思考過各種關聯的空間, 它通過一條非常細而不穩定的線來進行主觀和非主觀的表達。
出于同樣的原因,每種影像都包含了一種虛擬的效力或儲備,這是通過與其他 影像星座的聯系而實現的。這就是說,影像包含了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相互交換,因 為作為純粹記憶的虛擬總是不同于任何以穩定形式將其實現的具體影像。再一次 作為經驗、認知和影響的辯證催化劑,影像的效力不是為了證明現實,而是去影響 其他影像并為其他影像所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肯定,影像形成了一種 外化的主體性,一個記憶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正如柏格森所假設的那樣,時間被 理解為處于因果機制之外和時空線性的傳統標準之外的實現過程。
正如記憶涉及一個非個人的層面,它表明了一種外化的主體性,從吉爾·德勒茲 (Gilles Deleuze)以及福柯(Foucault)和布朗肖(Blanchot)所描述的角度出發,思想現在被理解為“外部的思想”(Deleuze 1986,126-127)。思想不再僅僅從意 識的主觀和心理機制的角度來考慮。正如羅德維克(D.N.Rodowick)在他對德勒茲 時間-影像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樣,思想作為純粹的虛擬性,或“絕對記憶”(Deleuze 1986,114),指的是與思維行為相關的絕對范疇,一種游離的力量,它包含了影像未 實現的力量(Rodowick 1997,201,180)。因此柏格森有句著名的格言:時間要么是 創造,要么是虛無(time is creation or is nothing at all)。
這里的關鍵之處在于對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思想行為的考慮,由于這個原因,它 一直有待完全實現,從而使主體面臨難以想象的思維困境(Deleuze and Guattari 1994,59;Deleuze 1994,140-142,1989,166-167)。換言之,主體面臨著一種思維 方式的失效,迫使他們更換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來擺脫絕對存在和系統表達的掌 控。正如羅德維克的解讀,德勒茲的時間-影像向我們展示了這個外部的絕對范疇, 它被定義為一個閾值空間,一個缺乏幾何視角穩定性的非人類的和去中心化的空 間(Rodowick 1997,188)。總而言之,歐幾里得空間(Euclidian space)探討了一 個主體特享的中心位置,被置于幾何三角中,最終為能夠處于拓撲或圖解空間中去 中心化的主體提供了一個位置,打破了對預先確定的關系和關聯的預見。
在這一點上,戈達爾的電影是極致的,它挫敗了由電影視覺構建的習慣性期 望,將其轉向了對影像中可以看到和發現什么的期望。戈達爾在《電影史》中建立 電影圖集的成功嘗試,與構建一種記憶裝置的必要性相對應,這種裝置能夠揭示 影像的混亂和強烈動蕩的區域,即它們跨越時間和地點的過渡、碰撞、轉移和去領 域化,這是瓦爾堡在他的《記憶女神圖集》中首先設想的。在這兩者中,圖集都成為 一種易讀性的工具,它揭示了理智與情感、狂喜與憂郁、生存與死亡、阿波羅與酒神 之間的對立力量。這些力量形成了一個由影像本身構成的動蕩區域,因為它們處在 一個“外部”區域:一個被認為是有待思考和實現的外部,超越了主體性和非主體 性之間的正統和二元對立。
戈達爾偉大而決定性的舉動是將這種外部空間轉移到電影屏幕上,使其處于一 種表面飽和的狀態,其中重要的是浮雕、曲率、速度以及視覺和聲音片段的疊加,被 認為是思想形成的基本要素。作者的觀點是,瓦爾堡和本雅明的歷史學說已經將外部 的思想納入思維和影像之中,在重塑思想與呈現的傳統模式的外化媒介中物化。瓦 爾堡的英明決定在于將非成形的關系的歷史外部轉移到圖像的圖集上,而本雅明的 天才之處在于從文本碎片的不規則節奏的角度來設想文化表現的多樣性,這些片段 受到多重主題偏離和檢查的影響,喪失了書籍形式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如果說在本雅 明、瓦爾堡和戈達爾那里,影像的概念是他們歷史學說的基本要素,這是因為對他們 所有人來說,影像被理解為它們產生辯證思維的能力:也就是說,它們具有調和矛盾 和不規范行為的能力,而非渴望觸及一個終極合題或一個包羅萬象且僵化的真理。
但不僅僅是這樣。對他們所有人來說,影像空間也是一個政治和倫理空間,是一個多元的、主體間的、異質的“閱讀與反閱讀、公眾與反公眾的代理”(Hansen 1992,71)。對他們所有人來說,影像的空間與思維導致的失憶的救贖有關。本雅明 正確地斷言柏格森對時間和記憶的思考中沒有任何歷史意義。他的意思是,人們還 必須考慮柏格森的記憶模型在對歷史時間的哲學和倫理理解中的相關性。對本雅 明來說,如同對戈達爾和瓦爾堡一樣,我們繼承的責任以及我們改造這些遺產的 方式是對記憶和時間最重要的表達,它為歷史提供了一種批判立場的意識,以及一 種從事旨在培養解放和永恒價值的活動。并非偶然的是,德勒茲的外部的思想也要 求將一種思維行為作為一種阻礙、創造和嘗試的因素加以考慮——時間要么是創 造,要么是虛無:因為簡化記憶和歷史主義的整體方案,就相當于發現和建立一個 轉換思維空間的行為,以對抗政治和社會文化領域的商品化和陳舊的審美化。
戈達爾將記憶理解為一種抵抗行為,并在《電影史》3A的一個段落中發展了這 一范式。在一段新聞短片中我們可以察覺到躺在地板上的尸體的存在,鏡頭的抖 動和迷失方向的運動反映出記者所體驗到的危險,其與馬塞爾·卡爾內(Marcel Carné)1942年的《夜間來客》(Les Visiteurs du Soir)中的片段剪接在一起,這 是一部關于記憶和愛的力量的電影,同時還剪接了播放慶祝巴黎解放的電視畫面。 其插卡字幕為“你必須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是真實的,什么是公平的”(Faut frapper que c’est vrai, que c’est just),并伴隨著畫外音:“又一個五十年, 我們正在慶祝巴黎的解放;也就是說,既然所有的力量都變成了一種奇觀,那電視 就組織了一場盛世奇景。”影片的結尾提到了詩人們,法國抵抗運動成員詩人克洛 德·羅阿(Claude Roy)和死于古拉格勞教營的俄羅斯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 (Ossip Mandelstam)。兩者都體現了“抵抗是詩歌的第一要務”的理念。正是在 這種背景下,戈達爾隨后與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建立了聯系,作為一種真正的電影抵 抗運動,能夠記錄這場災難并留下深刻的記憶。
歷史的幽靈和微弱力量
如果影像的政治和倫理維度是本雅明和戈達爾作品眾所周知的特征,那么事 實是,瓦爾堡在他的《圖集》(Atlas)中的第78和第79幅嵌板上——本文稍后會回到 這一點——在那里也證明了這種價值在其作品中同樣具有決定性。瓦爾堡也許是第 一個從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觀點中認識到歷史過往的重要性和表現 力的人,雅克·德里達后來將這一觀點概念化為一門幽靈學(hauntology),瓦爾堡 由此提出了形而上學本體論的一種新模式。通過涵蓋過往的幽靈表象,瓦爾堡開辟 了時間本體論在有關政治的記憶、遺產和代際方面的研究,將成為精神的肉體這一 德里達式的主題與影像和語言的不確定性聯系起來(Cf.Derrida 1994,5)。
通過將他的《圖集》定義為面向成人的幽靈故事,瓦爾堡強調了被壓抑者的幻 象生存,從而將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學中的幻象概念還原到歷史中。幻象,即使與精神分析的科學志向不相容的唯心主義實踐相聯系,也為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種壓抑 機制的影像和結構性的精神論式的重現;就瓦爾堡而言,則將其應用于對歷史地 形的解釋,涉及形象的遷移和變形。正如皮拉爾·布蘭科(Pilar Blanco)和埃絲 特·皮爾恩(Esther Peeren)所觀察到的那樣,幻象是一種強有力的隱喻,隱喻了 與他異性模式和存在的替代模式的相遇,交叉了顯然不相關的時間性,并產生了對 線性時間優勢的抵抗(Blanco and Peeren 2013)。和德里達一樣,在瓦爾堡的認 識中,幻象喚起了一個不可分辨和不確定的區域。它形成易于理解的知識的能力受 到了質疑,因為它指的是正常感知之外的東西,是作為被認可的過往的儲存庫的檔 案之外的東西,擾亂了本雅明經常描述的空虛和同質的歷史主義時間。
事實上,幽靈作為歷史認知的另一種模式,在本雅明和戈達爾那里也發揮著重 要作用。在影片《悲哀于我》(Hélas Pour Moi,1993)的開始,戈達爾引用了本雅 明關于歷史哲學的第二篇論文的法語版本中的一段話。這個片段由一個神秘的畫外 音喃喃自語:
我們的朋友們的聲音不是有時會與前人的回聲縈繞在一起嗎?另一個時代的女 人不也和我們的朋友一樣美麗嗎?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過往需要被救贖,而救贖 的一小部分恰好是我們力所能及的。逝去的一代和我們所屬的一代之間有一種神 秘的協定。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是已經被期待著的。
首先我要說的是,在戈達爾的作品中,正是影像所特有的出現-消失結構和對 解讀的封閉性的抵制,建立了看到和傳送過往的可能性。在《電影史》的1A、1B和 3B的引導段落中,戈達爾策略性地使用了幾段來自1993年的一部極具哲學和詩意的 影片《悲哀于我》的節選,這充分證明了費埃斯基-維維(Fieschi-Vivet)的重要論 點,即在戈達爾那里,美與神圣出現在詩歌和歷史的交會處(Fieschi-Vivet 2000, 190)。即便對戈達爾來說,“影像首先是救贖的程序”(3B),這是因為它包含了一 種時間觀念,在這種時間觀念中,過往是一種構成毫無疑問的實現的高度活躍的元 素。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將影像與現象學的‘本質’區分開來的是它們的歷史索 引”(Benjamin 1999a,462,N3,1),它帶有一種有效的和內在的潛能,“借由這種 潛能,它完成了所謂的救贖”(Benjamin 1969a,254)。
在本雅明第二篇論文的最后部分(未被戈達爾引用),我們讀到:“就像我們 之前的每一代人一樣,我們被賦予了一種微弱的彌賽亞力量,一種過往所具有的力 量。”(Benjamin 1968,254)屬于每一代人的微弱力量包含了本雅明在《神學-政 治學殘篇》(Theological-Political Fragment)中所描述的“世俗的節奏”;這是 一種不完美的、脆弱的、有限的救贖力量,它將帶領人類以最難以察覺的方式接近 彌賽亞的救贖。本雅明寫道:“正如一種力量通過在前進路徑上的運動,可以增強另一種相反方向上的力量一樣,世俗秩序也正憑借它的世俗性質促進了彌賽亞王 國的到來。”(Benjamin 2002,305)這里的關鍵是考慮一種不具有彌賽亞主義的 彌賽亞傾向,一種世俗的宗教信仰,賦予過往一種嶄新的高貴,在本雅明后來的作 品中,都是從反法西斯主義的堅定而緊迫的政治任務的角度來理解。
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emama)(2006,17)認為,這種本雅明式的微弱救贖 力量決定性地影響了戈達爾的《電影史》。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歷史是由力量 組成的,因為它指的是不間斷的和在時間中持續存在的事物,包括災難、受害者和 被壓迫者,即那些被歷史傳統的制約性權威和虛構的和諧過往的幻象系統地遺忘 的人。對于本雅明來說,對戈達爾也一樣,把過去被壓抑的主體和材料從占統治地 位的歷史傳統中解救出來,是唯物主義歷史學家的責任。最終目標是提供另一種歷 史暫時性,能夠紀念那些從未從歷史中獲得絲毫益處的人(Scemama 2006,14)。
現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瑟琳·席安瑪在本雅明的微弱的彌賽亞力量 (faible force messianique)和物理學中的弱核力(force d’interaction faible)之間建立了對應關系,她認為,這決定性地影響了戈達爾的蒙太奇和政治 電影制作。弱核力也被稱為弱相互作用,戈達爾在《電影史》3B中提到了弱核力。 弱相互作用是自然界四大基本力之一,它負責基本粒子的改變:例如,在源自原子核 的β粒子發射過程中,中子消失并被質子取代。正如瓦爾堡的動態圖解概念一樣, 戈達爾的影像如同粒子一樣發揮作用,其帶有正負能量的電荷在相互連接的網絡 中形成,并根據干涉視覺和聲音的影像排列的力場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影像的意 義是在這種關聯的不斷變化中遇到的,也是在這些變化的中斷中遇到的(Scemama 2006,12),暫停了一個瞬間,其中文字和影像的“可讀性”是“直接從蒙太奇的選 擇中產生的”(Didi-Huberman 2008,139)。回顧本雅明的定義,辯證意象對應于 這種“靜止的辯證法”(Benjamin 1999a,462,N2a,3),因此涉及一種思維運動, 在戈達爾看來,這種運動遠遠超出了動畫影像的機械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戈達爾對微弱力量的提及以參考亨利·朗格盧瓦(Henri Langlois)在法國電影資料館的實驗電影選編為背景,并對20世紀50年代末新浪 潮運動(其中包括戈達爾作為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出現產生了影響;還有 一個事實是對杰伊·萊達(Jay Leyda)、路易·德克(Louis Delluc)和謝爾蓋·愛 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等重要導演的電影只能加以想象,因為它們是被禁 止的或根本無法引進的,“真正的電影是無法看到的電影……因為它已經被遺忘, 仍然被禁止,總是看不到”(3B)。驅使戈達爾創作其首部電影的動機,至少部分地 是試圖恢復那種看不到的電影的精神,試圖恢復那些一直不為人知的部分,建立起 戈達爾與過往的對話,以及與那些先于他并給他以啟發的形式的對話。
戈達爾在回顧評價過程中認為,盡管如此,那些領導了反叛的法國新浪潮的人的 大膽應該被描述為,最準確地說,不是勇氣的表現,而是軟弱的表現。實際上戈達爾把這種弱點想象成與電影工業和電視有關的負極蠻力的正極,通過一段拳擊打斗的 視頻片段來隱喻地表現與特呂弗(Truffaut)和戈達爾本人等導演的新浪潮電影片段 相對立,以及將朗格盧瓦的肖像與宗教題材文藝復興繪畫中的神圣人物混合在一起。
這種參考網絡,也揭示了新浪潮的作者論(politique des auteurs),隱含了 電影的救贖維度的理念,不僅與自身斗爭(即與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奇觀和娛樂電影 斗爭),而且與電視的間離力量斗爭。“電影代替了我們對一個更符合自身欲望的世 界的凝視”(1A);但是,正如本雅明和瓦爾堡已經理解的那樣,人類的欲望和烏托 邦很容易被意識形態和權威力量制造的古老幻想和神話所欺騙。
戈達爾將電影史理解為一部歷經沉浮興衰往復的歷史,包括這一理念自身與 電影不完美的相遇;它的紀錄和想象的力量很快就被工業電影中男性化和有利可 圖的性和武器主題撕得粉碎,“電影就只是女孩和槍”;我們在1A中聽到:“全世界 只值五分錢。”但是,電影在文化工業和奇觀之手衰落的這種明顯嚴謹的邏輯,實 際上是一個更實質性和更重要的論點的基礎,這個論點和電影與20世紀歷史的失 敗結合有關,更確切地說,它在記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集中營悲劇方面無能為 力。正是電影對世界的承諾的失敗觸發了戈達爾的救贖追求,通過進行不斷的自我 批評和改造,他不僅要拯救現實和電影的記憶,還要拯救那些過往的無聲的受害 者,他們的幽靈不可挽回地糾纏著我們,要求我們重新關注和承擔責任。
形象將在復活的時候出現
在《電影史》1A的末尾有一個著名的段落,表現了喬托(Giotto)的《基督復活, 不要觸碰我》(Resurrection,1304—1306)中的抹大拉的瑪利亞(Mary Magdalene), 其被旋轉了90度。在喬治·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的影片《郎心似鐵》(A Place in the Sun,1951)中,這位人物呈現為來自天堂的天使,雙手環抱著伊麗莎白·泰勒 (Elizabeth Taylor)。伊麗莎白·泰勒和抹大拉的瑪利亞影像的疊化被雅克·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解釋為電影重生可能性的隱喻符號,在它未能記錄滅絕營的災 難之后(Rancière 2001,235)。可以肯定的是,畫外音通過對喬治·史蒂文斯的引用, 維持了這種疊化的意義(也與營地的鏡頭和戈雅[Goya]的《戰爭的災難》[Disasters] 的復制品疊化):根據戈達爾的說法,這位導演只能回到好萊塢與伊麗莎白·泰勒一 起拍攝幸福與和平的場景,因為在1945年,他決定使用柯達(Kodak)委托的第一批16 毫米彩色膠片,在被美軍解放的那一刻見證集中營內的暴行。
米里亞姆·海伍德(Miriam Heywood)已經證明,迪迪-于貝爾曼對朗西埃將伊 麗莎白·泰勒作為復活天使的隱喻性描述的強烈拒絕是一場人為的爭論。朗西埃的 解釋不僅在這一段落所提供的影像和評論中得到了完全的支持,而且在戈達爾更廣 泛的主題和《電影史》的指導方針中得到了支撐(Heywood 2009,275-276)。盡管如 此,迪迪-于貝爾曼對復活概念的否定在許多層面上提出了需要仔細分析的問題。
首先,人們應該認識到電影復活的力量對戈達爾的重要性。通過將復活的宗教 主題與俄耳甫斯(Orpheus)的古典主題相交叉(在2A中,戈達爾肯定了電影允許俄 耳甫斯回頭看他的妻子歐律狄刻[Eurydice]而不會致死的情節),戈達爾賦予了電 影紀錄影像的潛力,使我們得以瞥見不可能看到的東西。更具體地說,電影為我們 提供了對歷史苦難事件的一瞥,這些事件在范式上抵制了歷史研究的傳統方法和敘 事程序。對于戈達爾來說,電影的影像表達并沒有被因果和理性的聯系完全解釋或 耗盡,而是肯定了“一種非物質性的物質幽靈的矛盾情形”,被畫外音不斷地重新定 向和重新分配(Emmelhainz 2019,15)。因此如上所述,它必然意味著一個積極的、 富有想象力的、被解放的觀眾,其與阿多諾(Adorno)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一致,抵制文化和記憶工業的同質化和極權主義原則的邏輯。
戈達爾相信電影具有革命性的潛力,可以組織一個有助于解放的和有遠見意圖 的公共領域——這就引出了作者想在這里討論的第二個問題——他的理論方法不僅 與本雅明關于藝術品的可復制性的著作聯系在一起,而且與阿多諾關于電影的內在 集體性和多元性的推測聯系在一起。(至少有人愿意選擇聽從米蓮姆·漢森[Miriam Hansen]的建議,對阿多諾在電影和大眾文化上的立場進行另一種理解[Cf.Hansen, 1992])。然而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戈達爾對電影史的理解非常接近馬克斯·彭斯 基(Max Pensky)所認定的阿多諾對哲學“實踐失敗”的問題化。正如彭斯基所說, 根據阿多諾的觀點,只有當哲學錯過了它與世界的機會之窗,只有當哲學打破了它 對歷史現實的承諾,哲學才能“繼續存在”,并承載著有朝一日最終到達彼岸的希望 (Pensky 1997,10)。在戈達爾的例子中,這種消極的憂郁的目的與對電影的復活的 積極追求是交互的,電影是一個越界和“抵抗一種現實權力”的場所(Emmelhainz 2019,16)。對于從大屠殺的災難中創造“積極意義”(即電影狂歡式的復活)的倫理 風險,利比·薩克斯頓(Libby Saxton)表現出的不情愿(Saxton 2004,368)是適 當的,但一旦人們意識到——正如阿多諾對哲學的承諾——對于戈達爾來說,電影 處于對歷史的現實和自己的過往的永久欠債狀態,這種不情愿就會逐漸消失。
早在1993年的影片《孩子扮俄國人》(Les Enfants Jouent à la Russie) 中,戈達爾就宣布了電影的終結。但對于戈達爾來說,這種終結和失望的藝術也是 一種復活和希望的藝術(不清楚為什么迪迪-于貝爾曼在分析戈達爾的鏡頭時如此 斷然地反對這兩個互補的范疇)。因此對于戈達爾來說,這意味著要講述“所有從 未制作的電影的故事”(1A);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為了表達前大屠殺時期的電影在 尋找什么,但未能有效地說明和展示——從恩斯特·劉別謙(Ernst Lubitsch)的 《你逃我也逃》(To Be Or Not To Be,1942)到卓別林(Chaplin)的《大獨裁者》 (The Great Dictator,1940),以及讓·雷諾阿(Jean Renoir)的《游戲規則》(La Règle du jeu,1939)都是如此(Rancière 2003)。
因此,戈達爾是一位紀念主義者,他給自己的任務是追蹤電影和西方文化形象的路徑和命運,這些影像從根本上被理解為反映了整個世紀的動蕩和矛盾的歷史形 象(Rancière 2001,217)。正如席安瑪所指出的,對于戈達爾來說,后大屠殺文化的 每一個形象在其極限上,都浸透著對這一獨特而破碎的事件的記憶。因此,大屠殺 不僅必須從歷史失憶癥和奇觀與恐怖的邏輯中得到救贖(Scemama 2006,16),而 且必須從它與其他歷史災難相互依存的角度來解釋和記憶。如果“藝術在浴火中重 生”,就像我們在專注于抹大拉和泰勒的那一段落之前即刻聽到的(這是“藝術如同 火焰”這句格言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已經在上文分析過),這是因為藝術的形象和電 影的影像自身具有創造新背景的能力,用以理解難以察覺和未加思考的歷史。
這就是為什么戈達爾在《電影史》1B的開頭引用了波利尼安(Paulinian)的一 句格言,即“這個形象會在復活的時候出現”。攝影機鏡頭捕捉過往,通過死亡將 其定影。這取決于電影通過批判蒙太奇的潛力,即通過電影帶來的視覺和聽覺影 像之間的隱喻和轉喻共鳴來使其復原。戈達爾將歷史主題與宗教主題交叉,從而 提出了一種擴展的辯證蒙太奇,將電影影像與藝術史中各種形象的宗教主題相結 合,賦予電影以宗教和藝術所追求的普適特征。
如果戈達爾在《電影史》1B中將電影比作信仰的表現,這是因為電影的使命 是打破記憶儀式化的既有形式,將個人與歷史現實重新聯系起來。像宗教一樣,電 影對戈達爾來說是一種虔誠的實踐,使我們能夠理解對神圣的一瞥,因為“對神 圣實質性地發現和展示是電影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使命”(Fieschi-Vivet 2000, 203)。但神圣不是屬于一個形而上學的天空或者一個超然的世界,而是指對于歷 史主體、個人和集體來說什么是最真實的和最基本的。
作者認為,這種分析提出了第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迪迪-于貝爾曼在關于戈 達爾并非是“一個關于時間終結的神學家”的說法上是正確的(148)。但與此同 時,我們不能斷然地否決戈達爾有關歷史的作品的神學維度,對其他人來說,這構 成了戈達爾電影和本雅明歷史學說之間最典型的聯系點之一。
在戈達爾和本雅明那里,歷史服從同樣的宗教前提,即作為一種將人們與神聯系 起來的實踐。但這里的神性不是純粹的、絕對的或不可分割的。關鍵在于恢復人與殉 道之間的聯系,以及還原兩者之間的差異。戈達爾的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手相互接觸的 詩意形象恰恰指向了這種相遇,構成了一種形象轉喻的延伸,其中我們看到抹大拉的 瑪利亞和耶穌的手正要相互接觸但沒有接觸到,在視覺上喚起了虔誠和信仰的反應。 這里的問題是戈達爾對歷史的理解,歷史作為一個空間開啟了將個人與他人、與世界 聯系起來的可能性,反對由媒體和娛樂的影像所產生的異化,這些影像以標準化的行 為模式定義了什么是被期待的。因此,歷史包含了批判性思維的可能性和以我們為自 己構建的信仰和理念來定義自己的可能性。從隱喻的角度來看,歷史獲得了一種恰當 的神學和宗教意義,因為如果我們尋找“宗教”一詞的詞源,它似乎將我們與神重新 聯系起來,再一次,在戈達爾看來,神只不過是一種人文主義者視角下關于正義與民族間和諧的隱喻。它也是對電影作為我們在世界上信仰的更新這一理念的隱喻,因為電 影能夠創造歷史意義,即在一個集體的接受空間中培育批判性和情感思維的進程。
因此,通過將記憶的責任與正義的美德相結合,本雅明和戈達爾對政治的肯 定都反映在神學的成分中,賦予了辯證意象以形而上學的、精神的和神圣的維度。 本雅明將辯證意象與中斷的可能性聯系起來,因為它在集體經驗中引入了一種破 壞性的時間,包含了對歷史的彌賽亞式停止的需求,盡管如此,這絕不能與任何形 式的目的論的歷史頂峰相混淆。如果對本雅明來說,過去的可引用性伴隨著人類的 救贖,這是因為“只有對被救贖的人類來說,其過往才在它的所有時刻都是可引用 的。它活過的每一時刻都成為對《日程》(à l’ordre du jour)的引證——那一天 就是審判日”(Benjamin 1969a,254)。這同樣適用于戈達爾,因為他對電影采取 的引用方法與歷史的救贖是分不開的,通過這種方法,他試圖還原次要的微觀事件 和歷史行為人,反對歷史的統一,反對官方敘事的權威和意識形態的失憶癥。
情念程式或者女神沖動 對于戈達爾來說,歷史是一組多元且相互關聯的事件,作為分散的材料碎片, 通過蒙太奇的記憶實踐收集起來。但是,盡管在本雅明和瓦爾堡那里,蒙太奇仍然 受到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拼貼畫形式的啟發,但在戈達爾那里,這種關系通過 一種“反蒙太奇”被轉化和再造,正如朗西埃所說(2001,212,221),通過他實驗 性地使用視頻技術,其在影像與符號的融合中得以持續。 這就是為什么雅克·奧蒙(Jacques Aumont)認為,戈達爾的視頻蒙太奇讓他 發明了一種新的情念程式,如上文所述,瓦爾堡認為,這是一種強烈的悲情程式, 已經印刻在古典古代的形象中,隨后在文藝復興和現代藝術中重新出現。動作的強 度,擺動的姿勢和面部表情,所有這些由瓦爾堡通過感知和情感的具體化形式開展 的深刻感人的和充滿激情的調動都是由戈達爾從“純粹的能量形式”的角度采用的 (Aumont 1999,98)。
事實上,瓦爾堡和戈達爾之間一個最重要的相似之處在于這一共識,身體的 運動是一種有癥狀的“身體運動”(Didi-Huberman 2007,15),他們的情感程式是 對更廣泛的歷史動蕩和矛盾的表達。
例如在《記憶女神圖集》的第5幅嵌板中,瓦爾堡匯集了多種圖像,其中祈求、 絕望、憤怒和痛苦的情感表達典型地體現在一系列神話女性人物的姿勢中:從朱 利奧·博納索內(Giulio Bonasone)的蝕刻版畫《杰森和美狄亞》(Jason and Medea,16 century)中美狄亞的瘋狂動作,以及在濕壁畫《彭透斯之死》(Death of Pentheus,fresco,45-79 A.C.)中,女祭司們的暴力爆發,將彭透斯推倒并進行 肢解,到阿爾克提斯(Alcestis)和拉俄達彌亞(Laodamia)被哀悼的尸體,她們為 自己深愛的丈夫做出的犧牲與兇殘的母親的非理性暴力形成鮮明對比(《垂死的阿爾刻提斯》[Dying Alcestis,160—170 A.C.]以及《普羅忒西拉俄斯和拉俄達彌亞的 歷史》[History of Protesilaus and Laodamia,170 A.C.])。在第6幅嵌板中展現 了類似的主題,以公元前300年伊特魯里亞石棺(Etruscan stone sarcophagus) 中波呂克塞娜(Polyxena)的獻祭,以及公元前二世紀新式閣樓淺浮雕中舉著砍刀 跳舞的女祭司為代表,這些都表明對瓦爾堡來說,女神的歷史只不過是一部形象的 歷史,其流動關系到藝術史中形象更廣泛的歷史和文化的流動性。
作者認為,瓦爾堡和戈達爾對一系列身體姿勢的興趣,在他們對來自時間深處 的人類情感表達的認識中得到了轉化,是觀眾能夠理解和啟發式地解釋“歷史變 革和重現”的更廣泛的動力(Johnson 2016)。
因此,迪迪-于貝爾曼在《電影史》的福音場景中準確地識別出一種女神沖動(從 喬托的“抹大拉”的旋轉中識別出),并將其與本雅明對圣喬瓦尼洗禮堂中安德烈·皮 薩諾(Andrea Pisano)的《希望》(Hope)的描述以及對保羅·克利(Paul Klee)的《新 天使》(Angelus Novus)的描述聯系起來,這在本雅明的第九篇論文中成為對災難和 毀滅的寓言的著名描述(Benjamin 1968,149)。但迪迪-于貝爾曼在他的分析中誤解的 是,這種女神沖動最強烈的表現不是在抹大拉的旋轉形象中,而是在伊麗莎白·泰勒 本人的模糊運動中。更重要的是,她以一種介于上升與下降、神圣與世俗之間的姿態 被捕捉到,她的表現與瓦爾堡在他的《記憶女神圖集》第79幅嵌板中對喬托的《希望》 (Hope,ca.1305)的使用有著驚人的聯系,現在作者將要對這幅嵌板進行研究。
在第79幅嵌板左側鑲嵌的三幅畫作復制品中——拉斐爾(Raphael)的《博爾 塞納的彌撒》(The Mass at Bolsena,1512),喬托的《希望》還有桑德羅·波提切 利(Sandro Botticelli)的《圣杰羅姆的最后一次圣餐》(The Last Communion of St.Jerome,ca.1490—1495)——作者認為喬托的女神在嵌板的排布中至關重要,盡管 拉斐爾的這幅畫才是常規尺寸。當聚精會神地觀察時,就會發現有翅膀的人物發起的 運動似乎貫穿了整個嵌板,幾乎完美地相交于對角線上,在面板的右上角放置了兩份 舊報紙的剪報。第一份展現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簽署《洛 迦諾公約》(the Locarno Treaty)的時刻,他因此獲得了192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第二 份是一張報紙的標題,提到了德國拳擊手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他在職 業生涯的巔峰時期為希特勒效力,為雅利安人的種族優越論提供了粗暴的論據。
瓦爾堡對攝影記錄和其他非藝術材料的使用,以及對高雅文化的繪畫和雕塑 復制品的使用,在其創作《圖集》的時候為首創。此外,憑借圖像的辯證蒙太奇所 創造的意義,第79幅嵌板發展了一種以電影思維模式為特征的范式。從這個意義上 說,瓦爾堡的《圖集》在許多方面都預見了散文式紀錄片電影(戈達爾的作品是此 中的典范)的能力,它將來自不同來源、時代和文化的圖像異步地聯系起來,以傳 達西方文化的基本結構和動態。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影響給瓦爾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斯克爾-格拉斯(Schöell-Glass)證明,他的日記(Tagebuch)反復表達了對遍及德國和歐洲的反 猶太主義興起的嚴重關切,在同一幅嵌板上,瓦爾堡通過代表著對主的褻瀆的反猶 太人的宣傳的圖像暗示了這一點(Schöell-Glass 2001,201)。這幅嵌板還包括瓦 爾堡自己記錄的照片文件,其內容為在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庇護十一世(Pius XI)簽署《拉特蘭條約》(the Lateran Treaty)之后,圣彼得廣場上的紀念圣餐(詳 細記錄在第78幅嵌板上),教皇衛隊和意大利軍隊在場,象征著政治權威。
這些圖像顯示了大眾所盲從的法西斯主義修辭的宏大。然而最重要的是,它們喚 起了法西斯主義好戰言論對大眾的吸引力,從那時起,法西斯主義與墨索里尼一起, 將宗教犧牲的血腥敘事轉述到了政治領域(Querini 2016,17)。面對現代性的政治和 工業發展,它們正在迅速摧毀思想行為所需要的“距離感”(Warburg 1939,292),瓦 爾堡將藝術和文化的價值設想為批判性思維活動或思維空間的基本方面。正如戈達 爾一樣,在瓦爾堡的作品中,第79幅嵌板中寧芙女神的出現象征著一種思想和精神道 路,它允許人類保留一個“虔誠的空間和理性的范疇”(Warburg 1939,292)。正如本 雅明所說,一個圖像空間,在戈達爾那里,作為一種跨領域的實踐被授予了電影;而在 瓦爾堡那里,通過藝術史和西方文化形象的重復和遺存的循環來設想。
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瓦爾堡的《圖集》中,形象也獲得了明顯的政治 和社會共鳴。與本雅明和戈達爾的歷史學說類似,瓦爾堡更加認為低俗文化和高雅 文化的形象是歷史災難的潛在證據,也是構建歷史意識的公共空間的蓄水池。帶著 一種記憶的政治的緊迫感,辯證意象在所論三者那里都被解釋為基于當前世界的 歷史選擇和倫理參與模式來復活過往的催化劑。